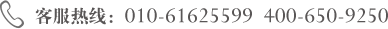專家解讀 | 靳樂山:我國生態保護補償法治化進程的里程碑
我國自啟動退耕還林工程,開始大規模生態保護補償項目以來,到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再到2024年4月國務院發布《生態保護補償條例》,標志我國生態保護補償法治化進程取得重大進展,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針對生態保護補償全面立法的國家。
《生態保護補償條例》發布,是我國總結過去25年來生態保護補償政策實踐經驗、提煉生態保護補償有效做法、穩定生態保護補償各方利益關系、明確各級政府和其他相關方生態保護補償責任的重要立法成果。
生態保護補償作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八項制度之一,結束了沒有系統立法的歷史,各級政府財政縱向補償有了法律依據和責任,地區政府橫向補償有了法律框架和規范,市場機制補償有了發展方向和空間。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生態保護補償有四“最”:生態保護補償力度最大、領域最全、法治化進程最快、對生態環境保護貢獻最顯著。
第一,我國生態保護補償力度最大
我國生態保護補償的政府投入補償的資金占比大,資金投入量逐年增長,這是我國政府貫徹環境保護基本國策的體現。據統計,中央層面補償資金規模由初期的幾十億元增長到如今的近2000億元,地方層面的補償資金已達到年均近千億元的水平。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國政府在生態保護補償領域的投入規模不斷增加,推動生態保護補償領域擴展、范圍增加、標準提高。如此規模的生態保護補償資金投入力度,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第二,我國生態保護補償領域最全
我國生態保護補償從最早的森林補償開始,逐步擴展到草原生態保護補償,到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水源區等水流生態保護補償、區域綜合補償(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等)、海洋生態保護補償、荒漠生態保護補償、濕地生態保護補償、耕地生態保護補償、水生生物資源養護補償,到目前,我國生態保護補償已經覆蓋絕大多數重要生態環境要素。
第三,我國生態保護補償法治化進程最快
國際上雖然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出現不少類似我國生態保護補償的生態系統服務付費項目,如法國的畢雷礦泉水水源地保護付費項目、美國聯邦政府的休耕補償項目以及紐約市的水源地補償項目,但是各國生態保護補償立法進程緩慢。目前世界上國家層面開展生態保護補償的少數幾個國家,都還沒有國家對生態保護補償或生態系統付費的全面立法。哥斯達黎加在《森林法》中有森林生態保護補償的條款,越南森林環境服務付費項目只是針對森林生態系統環境服務付費,秘魯“生態系統服務付費分配法案”中央政府并不提供生態保護補償資金,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CAP)也只是限于農業部門。我國開始生態保護補償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國務院通過的《生態保護補償條例》表明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在國家層面對眾多領域開展生態保護補償立法的國家。
第四,我國生態保護補償對生態環境保護貢獻最顯著
我國近20多年在生態保護補償方面的大力、持續和全面的投入,對我國生態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一方面提高了全民生態環境保護的意識,同時也貢獻于近年生態環境的改善。例如,我國自2003年開始實施退牧還草工程,2011年開始在全國8個省區開展的第一輪草原保護補助獎勵機制,到目前已經正在13個省區實施的第三輪草原補獎機制,顯著提升了我國草地整體質量,使我國從草原退化面積占總面積90%,轉變為植被恢復面積占總面積48%,草地綜合指標蓋度增加5.26%,北方草地植被凈初級生產力增加9.2%。我國流域環境質量穩步提升,2022年長江干流水質繼續保持在II類水以上,連續三年穩定保持這一標準,水質較以前明顯提升。我國持續二十年以上的退耕還林、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天然林保護等重大工程項目和政策,使我國森林覆蓋率從二十世紀末的18%,提高到2022年的24%,在世界森林覆蓋率總體下降的大背景下,我國森林生態保護成效卓著。
(靳樂山系中國生態補償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相關鏈接:
專家解讀 | 王金南 劉桂環:全面開啟生態補償新篇章 保駕護航生態文明新征程